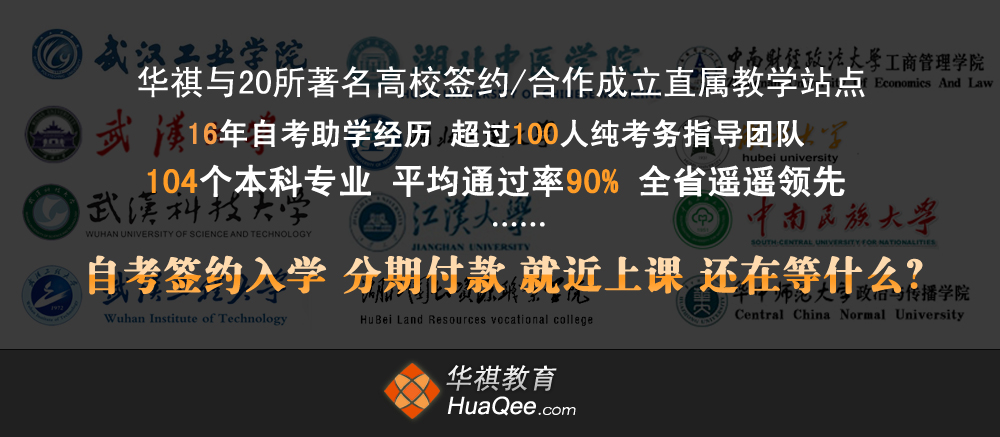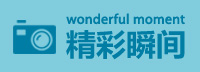中国只有一所教育部大学、大学去行政化、取消学校行政级别这样的话题,可以说,已经老掉牙了,在笔者看来,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要消除两大幻想,一是教育系统官员、行政领导的幻想,不能等待社会其他行业去行政化、消除"官本位"后,教育才去行政化,二是一线教育工作者和社会的幻想,不能再对行政部门主动推进去行政化抱有幻想,因为由行政部门主导去行政化改革,本就是一个悖论。这两大幻想的存在,导致去行政化知易行难。
我国于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要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可纲要颁布至今已经三年多,没有一所公办大学取消行政级别,就是新建的大学,也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包括宣称"去官化"、"去行政化"的南科大,也逐渐有了行政级别。去年11月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提到"逐步取消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
可以说,对于高校行政化的弊端,整个社会早已达成共识,不但导致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千校一面,难以培养有个性、创造力的学生,而且让整个大学陷入急功近利之中,由于权力不受制约,权学不分,近年来高校教育腐败、学术腐败高发,严重伤害大学的形象。我国从国家层面已经意识到推进教育去行政化的重要性,否则,就不会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了。
可是,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却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比如,对于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不仅官员反对,一些在任的校领导也反对,共同的理由是,如果学校取消级别,教育的地位会更低——没有级别的学校领导怎样和政府官员打交道,获得办学资源,另外,行政化的问题不独教育系统有,其他行业、系统的行政化也很严重,其他行业不去行政化,能让教育单独去行政化吗?换句话说,教育的行政化是官本位的缩影。
对此,简单地讲道理,比如去行政化不能观望,培养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公民的学校理性独立等,是不管用的,消除教育部门和学校行政等待整个社会去行政化之后再去行政化的幻想,最好的办法是明确时间节点,要求该去行政化的行业、系统统一取消行政级别,没有例外和特殊。这将打消继续保留级别的幻想。由于没有时间节点,总是把"逐步"挂在嘴边,也就没人相信会动真格。据报道,针对媒体"那具体有什么时间表呢?"的提问,袁贵仁部长表情也有些无奈,为此,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必须有明确的时间表,而且必须"一刀切"。否则,逐步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当然,教育部门会说,就是自己想取消学校级别,但权限不在教育行政部门,这是实情,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取消学校行政级别,仅仅是去行政化的一部分,而且如果只取消行政级别,而不改变目前的教育拨款方式、学校校长的选拔任命机制、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并没有改变教育管理模式,没有级别的学校,确实可能地位更低,另外,政府部门还可能套用级别对学校进行管理——目前在一些地方已经实行的校长职级制,就是这种情况。而在取消行政级别之后,改变拨款方式、实行新的校长任命机制,则是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做的事。这比取消行政级别还重要。
这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已有现成的模式,包括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拨款的预算,监督政府拨款,如此,学校就不必再"跑部钱进",看政府官员的眼神行事,只有有财政独立权,才有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公办大学理事会,由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办学战略决策,改变政府发文件、通知办学的方式;实行大学校长公开遴选,遴选校长不再按官员标准,而是按教育管理者、教育家标准;在校内建立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实行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权。
做到以上这些,根本不会存在取消级别降低学校地位的担忧,也不会担心学校拥有自主权之后滥用权力,而这只需行政部门坚定推进放权,完全可以做到,但遗憾的是,行政部门并不愿意放权,而依旧把财权、人事权这两大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过去三年中,教育放权也做了一些,但大多并不涉及核心的权力,而且,在有的权力下放之后,行政部门又会出台新的政策、规定,制造新的权力。可以说,去行政化最大的障碍在行政部门。
就这样,去行政化就只有表面的共识,而无实质的行动。如何改变这一局面?等待行政部门自觉放权是一方面,但这很难,更现实的路径是,要建立让行政部门必须放权的机制,目前,教育改革就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去行政化改革于是遭遇行政化的悖论,要走出这一改革困境,就应该改革改革机制,由全国人大讨论、审议教育改革方案,将教改方案变为教改法案,通过立法明细举办者、管理者、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并依法监督政府部门放权,这才能让改革顺利推进,而不是无奈的情绪、无谓的折腾。去行政化改革,必须抛弃幻想,不能再"逐步"了。